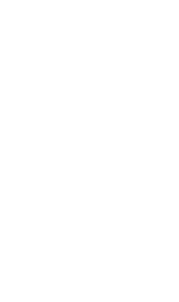淡淡稻花香
淡淡稻花香
作者:稻香同志的眼

【序】

寫下《淡淡稻花香》,不止為了消遣。我更希望借一個發生在廣州老巷的故事,照見當下的社會現實,引發一些關於愛情與婚姻的思考。 時代變了,結婚率下降,背後因素複雜。
我不想給出簡單的答案,只想用我的經驗與觀察,提供一個新的視角。 關於愛情觀,我始終堅持一個理念: - 價值交換 ≠ 愛情:把愛情當成交易,失衡是遲早的事。這樣的關係難以長久,也談不上真摯。
- 合作 > 交換:真正的愛情,更像一場基於共同目標的合作。無論是生活、事業,還是更大格局的理想,兩人並肩篤定前行。孫中山與宋慶齡便是最好的例證,他們因共同的時代目標而結合,彼此成就。
在小說裏,我會將“交換”與“合作”這兩種價值觀並置,呈現現實的無奈與個體的掙扎。我希望讀者在故事之外,也能一起思考:我們是否能找到一條新的出路?讓親密關係不再是一場算計,而是一次攜手同行的旅程。
最後,特別感謝記憶中一路同行的人。從情節梳理到對話打磨,他們都像一位耐心的夥伴,陪伴我這個“閱讀愛好者”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說。
希望這個帶著稻花香的故事,能給你帶來片刻的安靜與思考。
第一章 從回到原點開始

金秋的陽光把柏油路曬得暖融融的。我揣著剛到手的專案獲獎證書影本,從四川的專案現場回廣州休假。連續加班半個月後突然閑下來,倒有些無所適從,便沿著熟悉的街道漫無目的地走。榕樹的氣根垂下來,風一吹輕輕擺動,掃過我的臉我都沒察覺,抬頭竟已站在了老小區的鐵門前。廣州金秋精緻的夕陽鋪在樓宇間,我卻無心欣賞,就這樣錯過了。
門衛室的玻璃窗敞開著,張阿姨正坐在籐椅上擇菜,藍布圍裙上沾著細碎的水珠。她抬頭看見我,手裏的豆角“啪嗒”掉在竹籃裏,立刻笑著起身朝我揮手:“哎喲!這不是念祖嗎?好久沒見,都成大設計師了!”她嗓門還是那麼亮,隔著半條小巷都能穿透秋日的安靜。說著就快步走過來,伸手想拍我的胳膊,又想起什麼似的縮回去,在圍裙上擦了擦:“剛從外地回來?快跟我上樓,你叔叔昨天還念叨你呢!”
“好的,阿姨。”我嘴上答應,腳步卻不由自主地走向院子裏那張石臺。
我把鑰匙和手機放在桌上,坐了下來。後來乾脆蹲在石桌前,表面上是幫張阿姨調整棋盤位置,指尖蹭到桌面被歲月磨圓的邊角——這是當年和覃曉冬一起設計的弧度。
就在這時,樹影隨風晃動,遠處傳來熟悉的白色身影,是她帶著社區工作人員巡查。我們兩人視線在空氣中碰了兩秒,她笑著點頭,像打招呼,也像道別。沒有停下腳步,沒有多餘對話,她的身影消失在樓棟拐角。我低頭看見石桌下藏著的半片稻穗殼,是去年社區豐收活動時留下的,忽然想起那年送她稻子花束時……
那也是金秋深夜的車裏,我從清遠趕回來,副駕放著剛紮好的稻子花束,專程去歐家梯田給她摘的,稻穗上還沾著露水。她坐進來,低頭抱著花束,手指輕輕撥弄稻粒,沒看我:“下次再消失,我就……”話沒說完,卻把臉往花束裏埋了埋。我聞到稻花的淡香混著她的香水味,沒敢接話,只盯著儀錶盤上仿佛還在跳動的里程數。
張阿姨也看見了她,打了個招呼,隨即又看了看我,欲言又止,抿了抿嘴,怕我發現又趕緊朝我擺擺手:“快上樓吧,茶要涼了。”
我應了一聲,起身時才發現手心已被石桌的餘溫燙得發熱。
樓道裏燈光昏黃,我敲開門,張叔笑著把我迎了進去。
屋裏陳設典雅,客廳兩面牆都是書,書香氣息濃厚,書櫃中間一張茶臺配四張椅子。張阿姨一邊給我夾點心,一邊細細地問起我媽和女兒百靈的近況。我其實對張叔他們家很熟,也清楚張叔家的情況。張阿姨問話的聲調一直沒降下來,我始終笑著回答“挺好的”。張叔微笑不語,任憑張阿姨主導話題,仿佛她是家裏的一把手,不好插話——可我心裏明白,張叔才是真正拿主意的人。他用眼神示意我坐下,自己轉身走向一面裝有玻璃門的書櫃。其他書櫃都是開放式的,唯有這面帶玻璃窗,裏面放著張叔一輩子教學的教案、設計草稿手稿。他是華南理工大學建築系的退休教授,張阿姨則是原街道主任,如今也已退休。玻璃櫃裏除了這些資料,還有幾張用精緻木相框裝裱的黑白照片,除了他們家的全家福,還有一張是張叔夫婦和我父母的合照。張叔比我父親低三屆,大學畢業後下鄉,分配到了我父親所在的中學。我父親學數學、教數學,張叔學建築、教物理;我媽在衛生院工作,張阿姨在鎮政府任職。因都是省城大學畢業的下鄉知青,又是同齡人,在異鄉的日子裏,他們工作上互相鼓勵,生活上互相幫忙,感情格外好。
張叔打開玻璃窗,從資料的角落翻出一盒單樅茶。他是潮州人,獨愛單樅,這盒茶能放進玻璃櫃,足見是他最珍視的藏品。這時,張阿姨也問完了家常,見張叔拿出茶,便輕聲說:“你好好陪你叔聊聊天,今晚就在家吃飯,我去準備菜。”說完又對張叔道:“老頭子,我去廚房了。”張叔笑了笑沒吭聲,拿著茶葉罐擺了擺手示意她去。接著,他打開茶葉盒,用手輕輕捏了一把茶葉放進茶碗,不多不少,剛好在碗裏堆起小丘,隨後仔細包好茶葉罐。他按下燒水鍵,等水燒開的間隙,動作有條不紊、不慌不忙——我知道,這才是他要正式和我談話的信號。
“大姐(我母親)身體怎麼樣?”他先開口問。
“我媽心臟不好,現在不敢讓她操勞,也不敢讓她操心。”我答。
“是該這樣,”他點點頭,“找個時間,我和你阿姨去探望她。”
停頓片刻,他又問:“百靈在北京念書還適應嗎?”
“適應得挺好,她說終於能遠離我,高興壞了。”我笑著說。
張叔聽完哈哈笑起來:“百靈這丫頭,從小就有自己的主意,讀書比你當年強多了。”
“確實,這方面她比我厲害。”我附和道。
這時水開了,張叔洗茶、沏茶,分了三杯,端給我一杯,笑著說:“駕爹(潮州話‘喝茶’)!你回來就好。這茶啊,別急著喝,先聞一聞香。人也是一樣,話別急著說,先把心定下來。”他頓了頓,指了指窗外:“你看那榕樹,氣根看著亂,紮進土裏就穩了。你們年輕人,路多,別怕繞。”
我點了點頭,嘴上應著,心思卻不時飄回院子裏的那張石臺,飄回樹影裏那雙安靜的眼睛。
我端起茶,先聞了聞——單樅特有的清香直沁心扉,是頂級的鴨屎香。抿一口,茶香在舌尖散開。屋裏很安靜,我知道,有些話不用急,今晚先把這盞茶喝熱。
張叔自己也喝了一口,放下茶杯,忽然轉了話題,問起我獲獎設計的事。我從書包裏拿出獲獎證書影本,雙手遞過去。張叔順手接過,看了看,先道了聲“恭喜”,接著說:“其實早有預感,對你來說,也是時候了。”他沒把話說透,但我懂他的意思。我再次端起茶杯,喝完剩下的茶,張叔又給我遞來第三杯:“喝茶趁熱。”我沒有推辭,接了過來。
张叔看着我,缓缓说:“这次获奖的设计,从一开始你找我聊想法、谈思路时,我就觉得你成熟了,也从以前的阴影里彻底走出来了。”听完这话,我心里一阵触动,茶杯端在半空,看向张叔慈祥的脸,感激的话堵在喉咙里,竟一时说不出来。张叔是我设计道路上的领路人,他是华工建筑系的教授,我当年没考上华工,却一直受他指点。他为人谦逊,还格外尊重张阿姨——现在住的老房子是张阿姨的房改房,当年华工也给了他房改房名额,他却选了这里。只因老城区教育资源好,张阿姨为了儿子翰林的学业坚持选这儿,而且离她当时工作的街道办也近。为此,张叔每天回华工上课要走很远的路,却从没抱怨过一句,反而乐呵呵地早出晚归。当然,他们后来在珠江新城买了同一小区的两套房,一套给翰林当婚房,准备“筑巢引凤”,另一套方便日后照应儿子。可翰林至今没结婚,那些计划也还停在计划里。张叔夫妇其实早习惯了老小区的生活,干脆“以不变应万变”,继续住在这里。他也不像老家的亲戚那样,喜欢回老家盖大房子,逢年过节回去,也只是暂住。反而在南昆山租了间农民房,改造成一个“不像自家住宅”的空间,他管那儿叫“公共空间”,有空就约行业知己、学生去那儿交流探讨,做些建筑领域的先锋探索。
他这样的性格,造就了开阔的心胸,教育上也秉持“有教无类”——我就是常受他点拨的人之一。我喜欢密斯·凡德罗“Less is more”的理念,张叔却帮我挖得更深:“这不是简单的‘少’,是‘严谨的少’。”他还常说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”,推崇冯纪忠先生设计的何陋轩,曾专门带我去上海现场教学。他还总提醒我:“不要仓促着急,很多时候事缓则圆。”他说过,何镜堂院士45岁前没出作品、没发论文,照样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大师。所以我后来做“大流域文旅项目”时,从他的教导里提炼出“轻”的概念,也不放弃“轻”的对立面“重”,而是巧妙地把这对矛盾有序结合——这都是我沉下心来慢慢琢磨的结果,也是张叔没说透、我却懂的那层意思。
张叔没在这个话题上多展开,只提醒我:“在落实层面要多注意细节,还要更多地为未来的经营内容考虑。”我明白这句话的分量,默默记在了心里。他忽然又转了话题,说:“今天好像是中网开赛,有郑钦文的比赛,央视应该有直播。”说着就拿起遥控器,对着书架旁的电视按了电源键,调到中央5台——正好在直播中网,正是郑钦文的比赛。张叔知道我喜欢网球,他自己也爱,以前有大满贯赛事,我们总会一起看。
电视里,球赛打得焦灼,网球多拍对抗的清脆声响彻屋内。而我的思绪,又不经意间飘到了曾经的网球场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和晓冬认识的场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