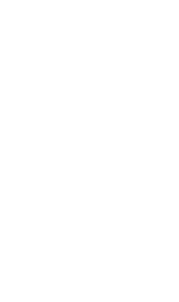淡淡稻花香
淡淡稻花香
本報連載小說
作者:稻香同志的眼
第二章 初相遇·網球場

傍晚六點的廣州,暑氣還沒完全散透,風裹著榕樹葉子的清香掠過社區網球場,把夕陽的金輝揉成碎光,灑在墨綠色的球網上。場邊的鐵架上,籌備組剛掛好“社區網球友誼賽”的紅色橫幅,塑膠繩被風吹得輕輕晃蕩。穿藍色馬甲的工作人員正蹲在地上畫發球線,退休的張阿姨也戴著老花鏡,在登記臺核對參賽名單,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,混著遠處居民樓飄來的飯菜香,透著股煙火氣。
覃曉冬站在登記臺旁,手裏捏著張皺巴巴的報名表,眉頭微蹙。她穿件白色速幹T恤,領口沾了點汗漬,深藍色的運動短裙被風輕輕一撩,露出修長的大腿,腳踝上貼著一小片創可貼——早上佈置場地時被鐵絲勾到的。作為籌備組副組長,她這幾天忙得腳不沾地,原本想報個女雙輕鬆些,搭檔李娜卻臨時變了主意,既要打女單,又被男朋友拉去湊混雙,檔期根本錯不開。“要麼報女單,要麼再找個搭子。”張阿姨抬頭看她,筆尖朝報名表上的“混雙”欄指了指,“我看翰林就不錯,你們倆同個中學的,他比你高兩屆,從小跟著他爸打球,大學還拿過校賽獎呢!”
覃曉冬愣了愣,張翰林這個名字她有印象,當年在學校運動會上見過他打單打,球風挺俐落。她沒多想,只覺得混雙能省點力,不耽誤籌備工作,便點頭應了:“行啊,那麻煩張主任跟他說一聲。”
可到了約定訓練的這天,覃曉冬提前半小時到了球場,先繞著場地慢跑了兩圈,又在角落拉伸——壓腿時膝蓋繃得筆直,小腿肌肉線條清晰,轉腰時T恤下擺輕輕揚起,露出一小截白皙的腰腹。等她把肩頸和手腕都活動開,太陽都沉到榕樹後面了,也沒見張翰林的影子。她正掏出手機想打電話,張阿姨的電話先打了過來,語氣裏帶著火氣:“曉冬啊,那臭小子臨時說有事來不了!我剛在電話裏罵他了,真是不靠譜,白費我一片心!”
覃曉冬握著手機,站在空蕩蕩的球場邊,有點尷尬。混雙名單已經報上去了,現在搭子放鴿子,連訓練都沒著落,比賽該怎麼辦?她踢了踢腳邊的網球,那球滾了幾圈,停在榕樹的陰影裏。
而此刻,張阿姨家的客廳裏,張叔叔正坐在沙發上看報紙,聽著老伴在電話裏罵兒子,沒吭聲。等她掛了電話,他才慢悠悠地掏出手機,撥通了我的號碼,聲音透著股穩妥:“念祖,在家嗎?帶上網球裝備來社區網球場一趟。我給你找了個混雙搭檔,叫覃曉冬,一起參加社區的網球比賽。你別擔心報名的事,張阿姨會跟組委會打電話改名單,她也會跟曉冬打過招呼的了,她現在在球場等你。”
我接到電話時,正坐在陽臺的籐椅上發呆,面前放著女兒小學時畫的畫——她畫了個紮馬尾的女人,旁邊寫著“媽媽”,又畫了個戴眼鏡的男人,寫著“爸爸”,只是兩個小人之間隔了好遠。離婚一年多了,我把女兒送到父母那邊暫住,高三了關鍵時刻怕她見到我也鬧心,自己守著空蕩蕩的房子,事業沒起色,生活也沒了方向,每天就這麼渾渾噩噩地過。聽到張叔叔的話,我愣了幾秒,既意外又有點恍惚,想起以前他總喊我去打球,便起身翻出壓在衣櫃最底下的網球包,拍了拍上面的灰:“行,叔,我馬上過去。”掛了電話,我又對著鏡子理了理皺巴巴的運動服,莫名有點緊張。
張阿姨看到張叔掛了我的電話,也沒顧上和老伴拌嘴,趕緊找出組委會的聯繫方式撥過去,語氣帶著點歉意又透著急切:“小王啊,麻煩幫混雙組改個名單,原先覃曉冬搭檔張翰林,現在換成徐念祖,資訊我等下發給你,辛苦啦!”確認名單改好,她才松了口氣,對著張叔叔念叨:“希望這念祖靠譜,別再讓曉冬空等了。”
走出樓道,晚風帶著榕樹的涼意吹在臉上,我才覺得腦子清醒了些。騎上電動車,十幾分鐘就到了社區網球場。遠遠就看見場邊的燈亮了,兩排白色的燈柱像串溫暖的小月亮,把球場照得亮堂堂的。覃曉冬正背對著我拉伸手臂,雙手舉過頭頂,身體向一側彎曲,白T恤貼在背上,勾勒出單薄卻挺拔的線條,深藍色運動短裙裹著纖細的腰肢,風一吹,裙擺輕輕晃著。
聽到腳步聲,她轉過身來,看到我,主動走過來,眼睛彎了彎,露出個淺淺的笑:“你是徐念祖吧?張主任跟我說過了,辛苦你特意跑一趟。你好,我叫覃曉冬。”她說著,自然地伸出手。我也馬上整理了一下背包帶,指尖在褲子上悄悄蹭了蹭,才禮貌地伸手與她相握。她的手溫暖而柔軟,指腹帶著點常年握拍磨出的薄繭,觸感實在又親切。我有些局促地開口:“你好,我叫徐念祖。那……以後我們就是混雙搭子了。”曉冬笑著點頭,聲音清爽:“是的,接下來這段時間要麻煩你多配合啦。”她的笑容像傍晚沒散盡的陽光,落在我心裏,讓那片陰涼許久的角落慢慢有了溫度。
“先別急著拿球拍,”她收回手,指了指球場外圈,“我們先繞場慢跑兩圈,再活動下關節,避免拉傷。我看你裝備挺齊全,以前常打球吧?”她說話時語氣溫和,像熟稔的朋友聊天,沒讓我覺得尷尬。
“哦以前打過,不過好久沒打了。”我放下裝備回答到,把球拍拿出來檢查了下拍線,又戴上帽子和護腕,重新緊了緊鞋帶,跟著她的節奏慢跑起來。晚風灌進衣領,帶著榕樹的清香,吹得胸口的沉悶散了些。跑過她身邊時,能瞥見她運動短裙下晃動的小腿,還有腳踝上那片小小的創可貼。跑完後,她又示意我一起做手腕繞環和肩部拉伸,指尖偶爾碰到我的手臂,帶著點微涼的汗意,卻一點不彆扭。等兩人都熱身完,她從球筐裏拿出兩個網球,走到網前:“我們先在小場對拉,找找手感,不用急著發力。”
她站在網前一側,拋球時手腕輕輕一揚,球慢悠悠地過網,落在我面前半米處。我握著球拍,手腕放鬆,輕輕把球推回去,力道沒控制好,球擦著網帶落了下去。“沒事,再試試,盯著球的落點,手臂不用太僵。”她笑著撿球,又發了過來。這一次我穩了穩心神,球順利過網,她再推回來時,我手感漸漸找回,慢慢能跟她打幾個來回。
等小場對拉找到感覺,我們才退到底線。她的底線球很穩,落點精准,看得出來有長期打球的習慣,是典型的女高水準。我心裏暗自發緊,想著不能辜負她的配合,也得拿出點狀態來。她發過來的球擦著邊線落進來,我快步跑過去勉強接住,可緊接著的回球還是失誤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擺擺手:“這球我的,沒跑到位。”撿球時抬頭,總能看到她站在對面等我,雙手握著球拍搭在肩上,風吹得她的運動短裙輕輕飄著,眼神平和,沒有一點不耐煩。漸漸的,肌肉記憶被喚醒,我回球的角度越來越准,偶爾還能跟她打十幾個來回,球拍擊球的清脆聲響,混著榕樹葉子的沙沙聲,格外好聽。
底線對拉練了半小時,她擦了擦額頭的汗,走到網前:“我們練截擊吧?混雙網前配合很重要,得有點默契。”她示意我站在她斜後方:“等下我喊‘封網’,你再往前補位,不用怕搶球,咱們互相補漏就行。”我按照她說的站好,她先接了個球,清脆地喊了聲“封網”,我趕緊跨步上前,剛好把對面過來的小球打回去。“漂亮!”她轉過頭沖我豎大拇指,笑容比剛才更亮,像把傍晚的餘暉都揉進了眼裏,“反應挺快,看來以前沒少打網前。”
之後我們又練了挑高球和高壓球,她挑球的弧度很足,給我留了足夠的扣殺時間,我跳起來扣殺時,她還會在旁邊提醒:“注意落地角度,別出界!”最後半小時才練發球和接發球,她站在發球區,拋球、揮拍一氣呵成,發完球還不忘調侃我:“你接發球姿勢挺標準,準備動作像德約,有點專業範兒啊。”我被她逗笑,也順著說:“那你發球這麼穩,我感覺像在跟莎拉波娃搭檔,賺了。”她聽完眼睛彎成了月牙,笑聲順著晚風飄開,榕樹葉子也跟著沙沙作響,像是在附和。
訓練結束時,天已經完全黑了。我收拾東西時,她已經把散落的網球都撿回球筐,還主動幫我把球拍放進包裏,指尖碰到球拍柄上的汗漬,也沒在意。“明天同一時間還來嗎?我們再練跑位和戰術配合,爭取比賽能順順利利的。”
“來!”我接過包,聲音比來時輕快了不少,“明天我早點到,咱們多練會兒。”
她背上自己的包,朝我揮揮手:“我家就在附近,先走啦,明天見。”她走得很輕快,深藍色運動短裙在燈光下晃出細碎的影子,很快消失在榕樹的陰影裏。
我騎上電動車往回走,晚風從耳邊吹過,帶著網球場上青草和汗水的味道。想起她指導我時認真的樣子,想起她笑起來時彎成月牙的眼睛,還有風吹動她運動短裙的模樣,心裏那片冷了很久的地方,好像被什麼東西輕輕焐熱了。摸了摸口袋裏女兒的照片,我突然覺得,或許明天,或許這場比賽,會是不一樣的開始。
第三章 比賽

第二天下午,我提前半小時到了球場。陽光從雲縫裏擠出來,像把老舊的黃銅把手擦亮了。風從東邊來,帶著潮味,吹得網繩輕輕顫。我在空場上做著熱身,先原地慢跑,再做肩袖的環繞,手腕繞圈,弓步壓腿。鞋底和地面摩擦發出細微的吱聲,像遠處有人在輕輕磨牙。
曉冬還沒到。我把背包放在看臺第一排,拿出兩瓶水,一瓶敞著口晾一會兒,免得太冷刺激胃。球包裏有她昨天讓我準備的護腕和備用吸汗帶,我按她的叮囑,把吸汗帶換了新的,纏得緊一點,末端用膠帶固定好。
她到的時候,我正對著牆練截擊手感。她背著包,肩上掛著工作證,手裏拎著一袋新球。招牌式的微笑像一塊被陽光烤暖的玻璃,亮而不刺眼。
“沒想到你提前了這麼多。”她說。
我把球從牆上接回來,沖她笑:“是的!比賽臨近我也想多練點,多培養點默契。”
她把球袋放下,開始做她的熱身流程。她的熱身很有章法,從腳踝開始,每個關節像被按順序喚醒。她不怎麼說話,只在需要我配合的時候用短句:“來幾個中速的正手,落點深一點。”“反手給我斜線,別太急。”“網前截擊我喂你,注意腳步。”
我太久沒打網球、沒參加比賽了,找回狀態是第一要緊的事,而重新學會集中精神,更是重中之重。畢竟我渾渾噩噩了很長時間——辦完離婚手續後,日子像被按了慢放鍵,連呼吸都覺得沉。注意力像一條受過驚的小魚,稍不留意就從指縫裏溜走。我盯著她拋球的手,數著節奏,儘量把每一次擊球都落在她指定的區域。
整個下午的訓練,我沒太多說話,幾乎所有的訓練計畫和細節都由曉冬安排。她的口令簡潔、清楚,偶爾會在我揮拍結束後提醒:“收拍再慢一點,別著急跑。”“重心別浮,落地再發力。”她看動作的眼神很專注,像在翻一頁熟悉的書,知道哪一行會有一個逗號。
我照做。不是因為我沒有想法,而是我知道,此刻的我最需要的是把身體和神經重新接上電。至於戰術和選擇,等“燈亮了”再談也不遲。
比賽的賽程是三十二支隊分八組,週末兩天打完。考慮到時間緊、體能要求高,賽制做了調整:小組賽為單迴圈,搶十一分分勝負,小組頭名出線;八強賽開始採用淘汰制,八進四打一盤、贏四局分勝負,平局搶五分;四強後為三盤兩勝,每盤贏四局分勝負,平局搶七分。第一天上午打小組賽,下午進行八進四;第二天上午半決賽,下午決賽並頒獎。
比賽那天天氣不錯。風小了些,陽光穩穩地鋪在場地上,像給每一條白線描了邊。簡單的開幕式之後,比賽正式開始。場地邊拉起了簡易的圍欄,幾位志願者舉著分組對陣表,喇叭裏迴圈播放著注意事項。
我站在邊線,手心有點潮。曉冬在我旁邊,拍了拍我的肩:“按訓練來。”
我點點頭。很久沒比賽了,狀態不及曉冬,而且我本就是替補搭檔,心裏早已定下“以她為主”的心思。比賽開始後,她很主動地溝通,也會直接提出想法和要求。她對贏的渴望非常強烈,對技術細節摳得很嚴格,能明顯看出這姑娘身上的一股狠勁。
第一局由她發球。她的拋球穩定,第一發球偏平,第二發球帶側旋,落點常常壓在對手的反手角。我站在網前,根據她的手勢調整位置。她的手勢簡單明瞭:拳頭表示搶網,手掌朝下表示讓我壓前,手指指向左側或右側則是她發球的目標區域。我照著她的思路來,比賽全程以保守、求穩為主。
小組賽的對手不算強。有一對配合生疏,發球節奏混亂;有一對能打幾拍漂亮的進攻,但失誤偏多。我們的策略是把球打深、打穩,逼對手先犯錯。曉冬在每一分結束後,都會簡短地說一句:“好的,再來一個。”“這一分別搶,等他失誤。”“網前別急,我來補。”她的聲音不大,但在場地上像有一個清晰的箭頭,指引著節奏。
我偶爾會在接發球上做些小變化,比如在對手第二發球偏軟時突然推一個直線,或是在網前故意讓球擦網過去。這些都是我觀察後做出的調整,但沒多說。我知道,今天的主角不是我的靈光一現,而是我們能不能把穩定的節奏保持到最後。
小組賽兩戰兩勝,我們以小組頭名出線。短暫休息後,下午進入八強賽。對手依然不強,我們延續上午的策略,順利闖進四強。
第一天的比賽結束後,曉冬來不及和我多溝通,只說:“不好意思搭檔,原本該好好慶祝進四強,也聊聊明天的比賽,但我在組委會還有工作,晚飯就不跟你一起吃了,明天見。”說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我收拾好東西也回了家。洗完澡,簡單吃了點東西就躺下了。比賽了一天,雖說不算太累,卻覺得時間過得飛快。難得有放空的感覺,我借著這股鬆弛勁,很快就睡著了。
第二天一早醒來,就收到了曉冬的微信。她說讓我們提前點到球場,聊聊四強賽的技戰術。我匆匆洗漱完趕到球場時,遠遠就看到了她——她比我到得還早,手裏還拎著早餐。
“還沒吃早餐吧?喏,給你的。”她見到我,直接把早餐遞了過來。
我還沒來得及說“謝謝”,東西就到了手裏。這時才發現,她自己手裏也有一份,顯然也沒吃。我接過早餐,一邊把吸管插進牛奶盒,一邊問:“那你打算今天怎麼打?”
曉冬嘬了一口牛奶,說:“我們四強的對手很強,我都認識,以前也打過,現在他們進步不少。我有點擔心……”
我笑著打趣:“你這麼有自信的人,也會擔心啊?有你這‘大腿’抱著,我挺安心的。”原本是想活躍下氣氛。
“哎,正經點!我是真擔心。我想聽聽你的意見——昨天我觀察你一天了,全程都是我說,你一句意見都沒提,是不是對我有意見呀?”曉冬忽然認真起來。
我原本咬了口麵包,打算細嚼慢咽,見狀趕緊吞下肚,咳嗽兩聲說:“不是對你有意見。”我低下頭,補充道,“其實昨天我觀察了對手,心裏有底,他們實力偏弱……而且你現場指揮得當,真沒什麼可挑的,結果不也贏了嘛。”
曉冬卻沒鬆口:“我現在更擔心今天的比賽了……其實你是在壓抑自己,有所保留,我能感覺出來。你很擅長觀察,尤其是對手的特點和弱點,昨天好幾個得分球,都是你針對性打出來的,但你得分後還是只聽我說,沒主動表達過想法。今天我不想再這樣‘我講你聽’,你好像有顧慮,一直在將就我,我們根本沒真正交流。我們是搭檔,該開誠佈公才對。我想贏比賽,但以我們現在的狀態,很難。所以我才擔心。”
曉冬其實很顧及我的感受,怕語氣重了影響我,越說越溫和。我這才明白她的意思,也覺得是時候放下包袱了。
“你說對了,昨天我確實有顧慮。怕辜負你的期待,所以一直以‘穩’為先,打得有點放不開。幸好對手弱,我們才順利過關,但說實話,從比賽表現和回球品質來看,我們根本沒發揮出平時的訓練水準。”
“就是嘛,你終於肯開口了!”曉冬的招牌笑容又回來了,“請繼續說,呵呵。”
我嘬了口牛奶,接著說:“既然你說四強對手強,我又沒跟他們打過,不清楚他們的球風球路,你先跟我說說——他們的特點是什麼?長處在哪?短板又在哪?”
曉冬稍微側過身,歪了歪腦袋:“嗯,男方很均衡,屬於‘六邊形戰士’,沒什麼明顯弱點,正手尤其強勢;女方個子不高,反手比正手好。他們的節奏很快,經常三個來回就結束回合。”
“哦,原來是這樣!”我想了想,說,“那就得讓他們‘毛躁’起來,失誤多了,我們的得分機會自然就有了——得分大概率要靠他們的失誤送分。”
“怎麼打?”曉冬追問。
“技戰術上,核心就是放慢節奏。我們站穩底線,把球的弧線打高,尤其是對手女方站網前時,多把球給到男方正手,讓他發力進攻,我們稍微往後站一點就能應對。女方個子矮是致命傷,我們的過頭球只要穩定,每一球來回超過六拍,時間久了,他們肯定會崩潰。”
“呵呵,你這戰術夠‘損’的!就這麼打!”曉冬咬著吸管笑了,我也跟著笑了。
半決賽的哨聲在上午九點準時響起。站在底線前,我能清楚看到對面男選手緊繃的肩線——他握球拍的指節都泛白了,顯然也知道這場比賽的關鍵。曉冬走到我身邊,用球拍輕輕碰了碰我的拍框:“按計畫來,別慌。”
第一局由對方發球。男選手的發球速度很快,第一球就擦著邊線落地,我勉強伸手夠到,回球卻有些飄。曉冬立刻上前補位,把球穩穩打回對方反手區。接下來的幾個回合,對方果然如曉冬所說,節奏快得像在趕時間,每一拍都想直接得分。但我們死死咬住,不跟他們拼速度,只把球往深區送,故意拉長回合。
打到第五拍時,對方女選手明顯急了。她原本站在網前準備截擊,見球又回到底線,腳步往前沖了半步,卻沒料到我突然挑了個高球。那球越過她的頭頂,落在身後的死角,她踉蹌著轉身去救,球拍卻只掃到了空氣。“好球!”曉冬在我身邊喊了一聲,聲音裏滿是雀躍。
這一局我們贏了。接下來的比賽,節奏完全被我們掌控——每當對方想加快速度,我們就用高弧線球把節奏拉回來;每當對方女選手靠近網前,我就故意打過頭球。打到第二盤時,對方男選手的正手開始出現失誤,大概是連續發力太多次,手臂酸了,有一球甚至直接打飛了。最終,我們以2-1贏下半決賽,挺進決賽。
中午的休息室裏擠滿了人,大家都在討論下午的決賽。曉冬原本坐在我旁邊看比賽錄影,突然有組委會的人來找她,說負責記錄成績的同事臨時請假,讓她幫忙頂一下。“我很快回來,”她起身時跟我說,“你先想想決賽的戰術。”
我點點頭,看著她匆匆離開的背影,拿起水瓶喝了一口。其實我已經看過決賽對手的比賽了——他們是上一屆的亞軍,男選手的發球和女選手的網前截擊都很厲害,整體實力確實在我們之上。
等曉冬回來時,離決賽開始只剩半小時了。她坐下來,擦了擦額頭的汗,直接問我:“決賽怎麼打?”
我放下水瓶,斟酌著開口:“我看了他們的比賽,水準確實比我們高……”
“我問的是怎麼打,不是水準高低。”她打斷我,語氣裏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緊繃。
我愣了一下,沒料到她會是這個反應。我以為她也看出了雙方的差距,便想緩和氣氛:“其實也沒關係,我們享受比賽就好。”
這話一出口,曉冬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。她沉默了幾秒,拿起旁邊的背包,聲音輕輕的:“你好好休息一下吧。”說完,她走到另一邊的座位上,拿出耳機戴上,再也沒跟我說過一句話。
我坐在原地,手裏捏著水瓶,心裏有些發慌。我不是不想贏,只是覺得沒必要給自己太大壓力——對我來說,能重新站在球場上,能打到決賽,已經足夠滿足了。可曉冬不一樣,她眼裏的勝負欲那麼明顯,我那句“享受比賽”,在她聽來大概像是敷衍。
決賽開始後,場上的氣氛完全變了。曉冬不再像之前那樣跟我溝通,發球前也不做手勢了。有一次我想跟她商量戰術,她也只是輕輕“嗯”了一聲,眼睛盯著對面的場地,沒看我。我們的配合變得生疏,原本能接住的球,因為缺少默契,好幾次都錯過了;原本能得分的機會,因為溝通不暢,白白浪費了。
對方顯然看出了我們的問題,打得越來越順。第一盤我們很快就輸了,第二盤也沒好到哪里去。當對方打出最後一個制勝分,裁判宣佈比賽結束時,我看到曉冬的肩膀垂了下來。她站在原地,盯著地面,好久都沒動。
頒獎的時候,我們站在亞軍的位置上。主持人念到我們名字時,曉冬勉強笑了笑,接過獎牌和證書。台下有人鼓掌,有人拍照,可我卻覺得那些聲音都離我很遠。我想跟她說點什麼,比如“下次還有機會”,可話到嘴邊,又咽了回去——我怕再說錯話,讓她更不開心。
比賽結束後,大家各自散去。我原本想約曉冬一起吃晚飯,跟她道歉,她卻先給我發了微信:“街道辦和組委會還有善後工作,晚飯就不跟你一起吃了,以後再約。”我看著那條消息,手指在螢幕上敲了又刪,最後只回復了一個“好”。
我一個人走到附近的小食店,點了一碗面。面上來的時候,手機響了,是張叔發來的微信:“祝賀你們拿了亞軍!要不要來我家吃飯?”我看著消息,心裏暖暖的,卻還是回復:“謝謝張叔,不用了,有點累,想早點回家。”
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翻來覆去睡不著。比賽的細節早就忘了,腦子裏全是曉冬的樣子——半決賽贏了之後她眼裏的光,決賽前她緊繃的嘴角,頒獎時她勉強的笑容。我知道我們之間有分歧:我在意的是重新打網球的快樂,她在意的是比賽的輸贏。可我沒料到,這點分歧會讓我們變成這樣。
接下來的日子,我沒再跟曉冬聯繫。我的生活像往常一樣,重新拾起網球,偶爾約以前的球友去球場打球。只是每次站在球場上,都會想起和她一起訓練、比賽的日子,心裏總有些空落落的。